2022年10月28日厦门大学历史系南强世界史系列讲座诚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员刘健教授发表题为《古代两河流域新年节日中的王权实践特征》的专题讲座。讲座主要围绕三个部分展开:一、古代两河流域文献中的“新年”节,二、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王权,三、新年活动中的王权实践。须注意,两河古代的“节日”(EZEM, isinnu)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节日,而是具有更加明确的宗教仪式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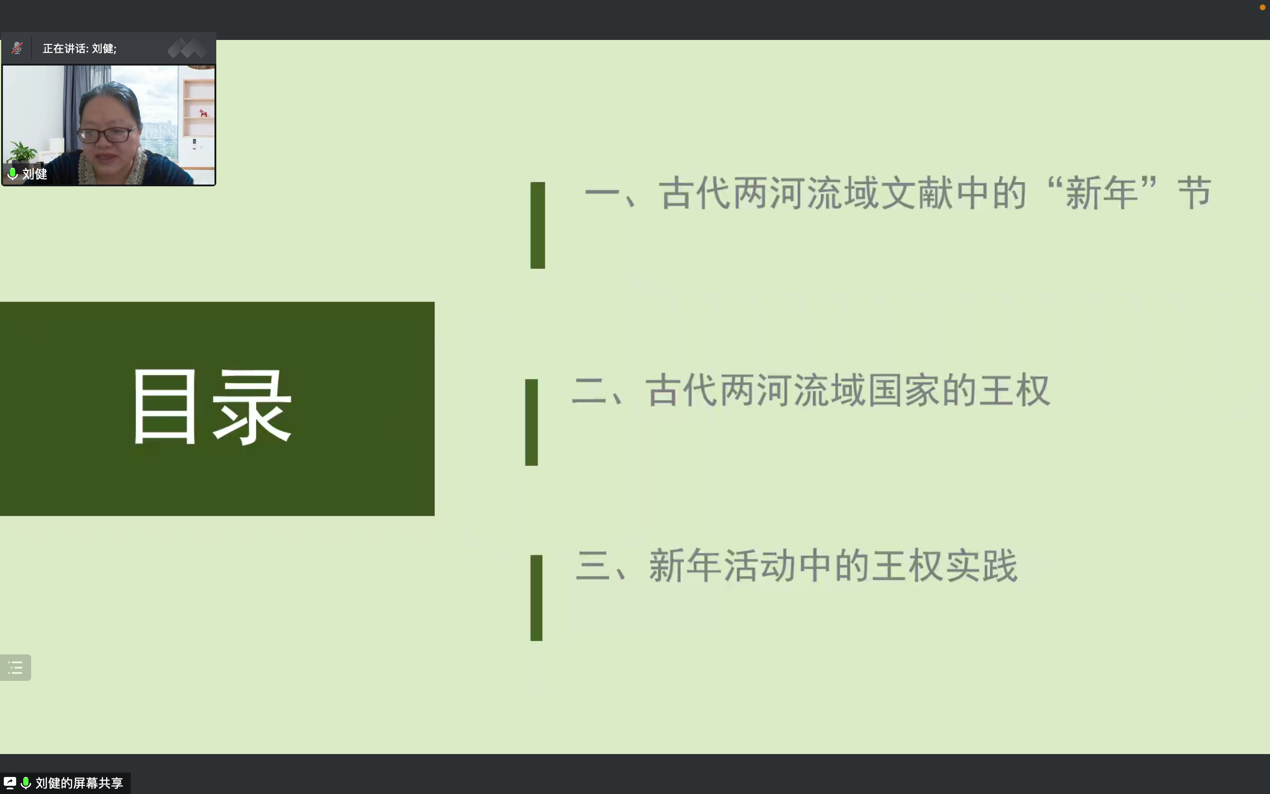
在第一部分中,刘健教授先从史料学的角度,主要列举了两类有助于还原新年节习俗的文献。第一类文献为对于新年流程的记录,典例从早到晚依次有三批,分别是:早王朝时期拉伽什(Lagash)在丰收季节对于南塞神一年一度的供奉,由于奉献谷物之日位于温马地区历法的首月,因此可以将神明品尝新谷的节日视为“新年节”(苏美尔语称’zag-mu’,即‘年之交’)。其次为乌尔第三王朝的对于南塞的赞美诗,尽管这是一篇文学作品,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恢复出新年节上的甄别仪式(即神职人员的年度考核),“女神”(以女神的名义)会下令开除祭器不洁、长明灯不亮、诵经中断的“šita-eša祭司”,僧侣膳食分配不公的“susbu祭司”,还有咏唱圣歌欠佳的“saĝĝa祭司”。最后则为出自塞琉古王朝、但是内容反映出新巴比伦风貌的仪式文献;这时的新年节被称为“akītu”,尽管其原型可以上溯至中巴比伦时期,亦曾传播至新亚述帝国上层,但相对完整的流程记录却是出自希腊化时期。第二类文献为年代记以及年表中涉及“新年节”的条目,这些文献仅仅只是提及而已,但缺乏细节描述,不过依然能给我们提供新年节的关键线索。代表例子有埃萨尔哈冬的年代记,其中记载公元前689年,当新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将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像被掠夺至阿舒尔城,此后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新年节都未能举行,这说明神像在仪式活动中必不可少。此外,涉及新巴比伦帝国的编年史让我们了解到,由于末代君主纳布尼德常年不在首都,而是驻守南部抵御阿拉伯人的要塞泰马,新年节也因国王的缺席长期中断。除了上述两类文献之外,一些神庙的经济管理文献(比如新巴比伦时期乌鲁克城的神庙供品清单)或是各种反映宗教观念的文学作品也能帮助我们了解到更多关于新年节的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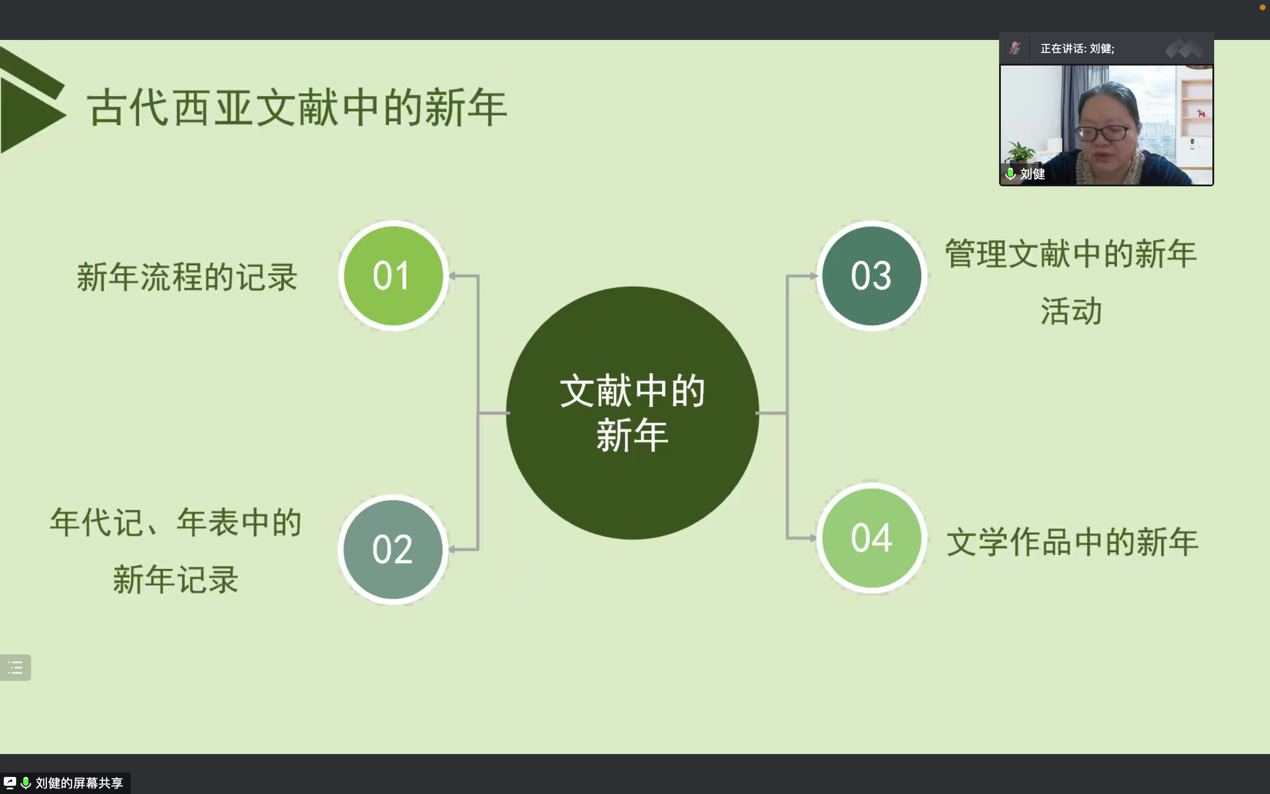
介绍完史料来源之后,刘健教授特别提及了“akītu”(新年节)的名称由来。尽管一般用阿卡德语的“akītu”一词指代第二千纪末以降的巴比伦节日;但其实第三千纪乌尔城的苏美尔语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作为节日的“á-ki-ti”一词(由‘时间’加‘大地’加‘接近’三词组成,含义不明)。不过需要注意,彼时的“á-ki-ti”并不能直接与新年节划上等号,而是一年举办两次(一月和七月)、用来庆祝谷物一年两熟的节日;与此同时,在特定的语境下“á-ki-ti”也可以直接用作月名,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乃是一年中的第七个月(起初为第六个月)、同时也是年名法纪年的岁首。尽管此“á-ki-ti”非彼“a-ki-tu”,但前者已经有了后者的影子,在丰收之际、祈求国泰民安的传统也确实影响到了后来的新年节。
接下来则为我们简要梳理了新年节的大致流程,相关场景主要涉及新巴比伦的新年节——“akītu”。首先须明确两河流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岁首设置不尽相同,比如阿卡德王国时期温马的岁首换算成今天的时间大致在夏至(冬季播种的麦子此时收获)、古巴比伦时期西帕尔的岁首在秋分、而依阿舒尔历法亚述的岁首则在冬至;而新巴比伦的第一个月则名为“nisannu”,并且与今天一样以一月作为岁首,只不过当时的“一月”大致对应公历的三月到四月之间(按:有别于最初品尝新麦的季节)。而新年节的大型庆典并不在一月一日就立即开展,前三日的仪式活动率先由专门的祭司(šešgallu)负责,于元旦的日出时分(约六点)为神王马尔杜克及其妻子举行仪式,之后每天的仪式开始时间依次提前,第二日为凌晨四点、第三日为三点二十、第四日为二点四十。而在第四日这一天,祭司要在马尔杜克面前朗诵创世史诗“Enūma eliš”,并且国王也从这一天起加入仪式活动,并从马尔杜克之子纳布的手中(象征性地)接过权杖。第五日仪式则于两点整开始,此后开始时间便不再提前;而上述仪式时间依次提前的过程被称为“dīk bīti”,即“唤醒神庙”。唤醒神庙之后,全国各地的“神明(塑像)”也会陆续来到巴比伦城;抵达之后,第六日便开始举办神像的大游行,游行沿着城市中心长约一公里、宽约六米的大道,目的地则是马尔杜克的埃萨吉拉神庙(Esagil);第七日则继续巡行至大庙附近稍小的“akītu之屋”。游行的同时还伴随着各种礼乐歌舞表演以及宴会活动,普通民众也能借此机会一睹平日在神庙内龛秘不示人的神像,一旁的戏剧演出则表演创世神话的相关情节。第十一日神像再次回到埃萨吉拉神庙,像创世神话结尾一样赠与神王马尔杜克祝福,同时马尔杜克也会决定人类国王的命运。第十二日仪式正式结束,全国各地云集的神明各自返回其居所。
在重现了巴比伦新年节的仪式过程之后,刘健教授勾勒了古代两河流域王权的基本特征,并概括为国王分别作为祭司、武士、牧者以及建设者的四种形象。作为祭司的国王,典型的例子就是乌尔南塞:他为南塞女神修建神庙、装饰神像,通过脏卜选拔高级祭司“南塞之夫”(dam dnanše),并让来自迪尔蒙(今巴林)的船只为他运来建筑用的木材。正因为国王作为神明虔诚的侍者存在,我们遂能在汉谟拉比法典的浮雕、马里王宫的壁画中多次看到国王从神明手中接过绳与杆的图像,这一图像鲜明地出了王权神授的内涵。作为武士的国王则大量出现于亚述的艺术作品中:尼尼微的宫殿饰板经常刻画国王猎杀狮子的形象,另据阿舒尔班尼帕二世的自述,他一生总共狩猎了多达二千余头狮子;而对外征服扩张也是彰显国王武力的关键环节。作为牧者(sipad,牧羊人)的国王,则应合《尚书》中“为天牧民”四字,表现出统治者应当爱惜民众的政治思想,具体则体现在乌鲁卡基那改革铭文中使强不凌弱的主张。作为建设者的国王除了修建神庙之外,也要注重沟渠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 ,刘健教授主要从正统性(合法性)、权威性、神圣性等关键词出发,提供了她现阶段初步的思考结果,以下对原文作简要摘录:早期两河流域人的新年观念就是庆祝丰收,感谢神祇的赐予;由此引申出庆祝新一轮的农事和农时开始的象征性仪式活动,体现出王权观念中狩牧万民的特征。各种宗教仪式、祈福与祭祀活动,王室及神祇列队游行,朗诵创世神话、为新年占卜、重演诸神战争等,综合体现出王权的神圣性、正统性和权威性。在诵读和表演神话史诗的活动中,表现宇宙秩序得以重新确立和巩固。游神仪式展现辽阔的统治疆域、稳定的国家统治;来自全国各地的众神共襄盛举,共同祝福国王统治稳固、国泰民安。通过宴飨活动,国王与民同庆、与民同乐,凝聚感情,增强民众的认同感。游神活动在开放的城市大道上举行,开放的空间、壮观的游神队伍、人头攒动的观众,彰显着普天同庆的节日氛围。新年庆祝活动万象更新的观念也反映在世俗的政事活动中,新年也因此成为了文书档案、年度财政重新开始的日子,也是神庙落成、国王登基的重大日子。

讲座的最后讲解了 “命运决定”仪式这一具体案例,给予王权实践以更为丰富的内涵。无论如何,“命运决定”仪式无疑是所有仪式中最为奇特的一环。自1921年法国学者(François Thurau-Dangin)在《阿卡德仪式》一书中发表以来,学者对于这一仪式的内涵莫衷一是,因为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国王在此时似乎遭到了祭司公然的羞辱——当国王抵达贝尔神(既马尔杜克)面前后,(国王的)徽章(从屋内)撤出,接着还有权杖、绳圈与兵器,他(祭司)拿着王冠、放到贝尔神前面的祭台上,他出去了。国王的脸颊“他”(祭司还是国王自己?)打着……他放在他身后,他让他进来到贝尔神面前……他的双耳,他让他跪在地上……国王(将以下的话)说一次:“天下邦国的主人,我并未犯下罪过,我并未忽视您的神威,我并未令巴比伦陷落,我并未宣告其分裂……”……国王的脸颊他打着,倘若他的眼泪流下,贝尔神便心情愉悦。倘若他的眼泪没有流下,贝尔神便怒火中烧,敌人将兴兵作乱、致其灭亡。而仪式结束以后,国王将重新佩戴好他的一身行头,恢复人前的体面模样。原文表意晦涩,而且残损严重,试问在仪式上祭司真的扇了国王的耳光吗?而国王又为什么要跪在神王马尔杜克面前一边自我辩护、一边堕下眼泪?刘健教授认为亵渎国王的仪式本质上还是对国王权力的重申与加强,但两河的王权观念似乎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讲座也留下了开放式的结局引发听众作进一步思考。
撰稿整理|雷智淋、李洹
审阅|曲天夫